
《囚车骑士》插图。《囚车骑士》出自12世纪法国特鲁瓦的克雷蒂安之手, 围绕亚瑟王王后桂乃芬与骑士兰斯洛的婚外恋情展开。克雷蒂安是中世纪传奇的主流——亚瑟王系列的主要奠基者, 作品影响深远。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英勇骑士兰斯洛(Lancelot)听说了邪恶的王子梅勒刚(Meleagant)将亚瑟王的王后桂乃芬(Guinevere)掳走了,便二话不说,拍马就去营救。在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赶着囚车的侏儒。兰斯洛向这名侏儒询问王后的去向,但是傲娇的侏儒却告诉他,除非他肯钻入囚车受辱,否则他不会带着他去找王后。高傲的、在战场上无人匹敌的骑士兰斯洛是何等身份?而在当时,囚车又是最低贱的去处,别说骑士了,就是仆佣杂役都以进入囚车为耻。可结果呢?兰斯洛却毅然钻进了囚车,然后又经过种种曲折,总算找到了被梅勒刚扣留的王后。
这是特鲁瓦的克雷蒂安(Chrétien de Troyes)写作于12世纪的《囚车骑士》(Le Chevalier de la Charrette)中的一个高潮。
这个故事并非是最早的英雄救美的故事,甚至也不是最精彩的,希腊的英雄们要早兰斯洛几千年就在为争夺海伦而围攻特洛伊,其宏伟壮丽的背景与生动感人的情节都不是这个小故事能够比拟的。然而,这个情节却蕴含着中世纪骑士文学中最独特、最经典的一种意识形态:典雅爱情(或曰宫廷爱情,courtly love)的精神。
女性至上,爱情第一
广义上的骑士,自古就有。骑士这个专有名词的拉丁语词源是miles,最初强调的是步兵而不是骑兵,同时还包含有服务、效劳的含义,后来才有了跟马之间的关系。然而真正聚焦到发源于中世纪欧洲、形成一种被后人冠之以“精神”之名的骑士群体,其范围则要狭小得多。到了中世纪,miles作为“骑士”的含义才渐渐明晰起来,开始被用来指代高等贵族。Miles与法语chevalier和德语ritter的关系仍然有待研究,但这三个词均指那些来自社会底层、但仍有晋升机会的人。尤其是chevalier,它最初就包含了miles一词中与马的关系,最早出现在1100年后的中世纪“英雄史诗”(Chansondegeste),后来由于骑士文学在英法宫廷的推广,而成为最广为人知的“骑士”专用名词。可以看出,此时的骑士已经包含了“贵族”“英雄”等光环。
之后,我们就看到了真正与文学结合起来的骑士。中世纪有着大量的英雄史诗描写伟大骑士们的故事,战场厮杀、勇斗怪兽与政治角力都是常见题材,但是,真正蕴含着后世称道的“骑士精神”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所谓“骑士爱情文学”或者“典雅爱情”文学才是我们要真正讨论的对后世的精神世界产生重大意义的文学体裁。像《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熙德之歌》这类纯粹的英雄史诗,虽然对文学传统也有重要影响,但其只是在文学序列中起到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而没有思想意识上的重要转向意义,而且这些史诗常常被用于宗教精神的弘扬与民族国家的政治宣传,所以并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那么,这种骑士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发明典雅爱情(或翻译为宫廷爱情,amourcourtois)这一专用术语的法国学者加斯东·帕里斯(GastonParis)的归纳,宫廷中的骑士爱情应该有如下四个特征:
1.这种爱情是非法的,需要秘密进行。比如兰斯洛和桂乃芬的感情,显然是非法的,也不是亚瑟王所知道的。
2.男人的地位是低下的,而女人则地位高尚,并且傲慢轻蔑。男人必须服从女人。
3.男人须努力通过自己的英勇、美德和奉献来赢得贵妇的青睐。
4.这种爱情是具有独特游戏规则的“一门艺术,一种科学,一种美德”(un art,une science,une vertu),相爱的情侣必须掌握这些游戏的规则。
这是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女性至上,爱情第一,偷情更让人兴奋,而且——得有一套仪式和规范。
没错,女性是完美崇高的,骑士必须拜倒在女士面前,必须对她言听计从,不得违背,为了她的指令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兰斯洛就是该放下自己的尊严,钻入囚车,为自己的女主人,为爱情而煎熬受苦。
虽然在学术界内,这种界定依然存在争议,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爱情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后来人附会的浪漫幻想,然后无论是在《囚车骑士》这样的短篇文本中,还是在《爱的艺术》《玫瑰传奇》这样长篇文学中,这几种特征都得到了彰显。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男性对女性屈从的意向即使在遇到社会习俗的桎梏之下依然能够畸形演化成“骑士风度”这样在后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观念,其中的内核之不虚应该可以确证。
挑战中世纪基督教厌女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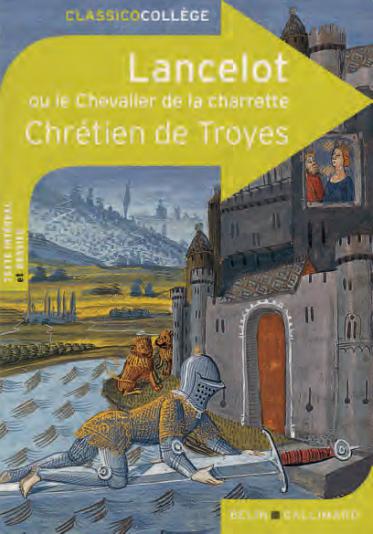
《囚车骑士》封面。书中蕴含了中世纪骑士文学中最独特、最经典的一种意识形态:女性至上,爱情第一。兰斯洛就是该放下自己的尊严,钻入囚车,为自己的女主人,为爱情而煎熬受苦。
在《囚车骑士》中,克雷蒂安又在另一个情节中考量了兰斯洛对女士的爱情以及崇拜同宗教信仰的关系。当兰斯洛找到桂乃芬之后,由于受到了梅勒刚父王的善待,他们暂住在他的城堡里,到了晚上,这两个情人终于按捺不住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兰斯洛翻窗而入。“然后他来到了王后的床边;兰斯洛弯腰向她表达了崇敬,他从没有对任何圣迹表达过如此的信仰……离别的痛苦是如此深刻以至于起身就是一次真正的殉道,而他则忍受了殉道者的苦难。”
在这段话里,兰斯洛似乎是在以一种爱的宗教代替了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他竟然把一个世俗女人的身躯抬高到任何圣迹都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他对她出自爱情的崇拜竟把基督教的崇拜也抛在了脑后,最亵渎的是,他竟然把离开一个女人的肉体当作了一次殉道。这种把极其庄严的基督教象征拿来与女人、肉体以及情欲做对比,是显然的对中世纪基督教厌女症的一种挑战。
故事的另一个高潮出现在竞技场上,英勇盖世的兰斯洛自然是无人可挡所向披靡,很快就赢得了全场的注目和赞誉。但是就在此时,为了确认兰斯洛真正身份的桂乃芬下达了让他故意输掉比赛的命令。处于万众瞩目巅峰的兰斯洛,如果突然变得不堪一击,输掉所有比赛,那他所受到的鄙视和嘘声会远远胜于一般骑士。这种羞辱对于一般骑士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那站在全场聚光灯下的兰斯洛该何去何从呢?
“一接到这个命令,兰斯洛说他非常乐意这么做,因为他只愿意取悦王后一人。”他遵命故意输掉了比赛。
在他看来,他的女士是无比完美的存在,而爱情是他行事的最高标准,并将这个标准放在了骑士视之为生命的荣誉之上。他相信:“毫无疑问,那服从爱情命令的人是高尚的,他所做的一切都应该被原谅。”
这几个段落,完整地展现了兰斯洛是如何完美体现了典雅爱情的特征的。现在,什么价值观在兰斯洛心目中最为崇高就不言而喻一目了然了。而他也成了宫廷骑士文学的代表人物,成了一名读者心目中光辉耀人的真正骑士。
这种骑士,不再是只有武力的勇士,看起来感人至深,但考虑到其背景,这整个故事确确实实十分诡异。
骑士群体真的存在
事实上,中世纪的欧洲,正是厌女症甚嚣尘上、登峰造极的时刻。所谓厌女症,在某种意义上又被称作反女性主义(antifeminism),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对于女性的憎恶、恐惧、诋毁和贬低的行为及言语。在西方文明史上,这种厌女的情结通常表达为用语言对女性的肉体、精神多方面的诋毁;并据此在现实中拒绝给予女性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对于中世纪来说,源自古典神话(赫拉、潘多拉、海伦等形象)、古典哲学(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厌女症)以及基督教的传统,都对女性从肉体形象,到精神气质,再到社会地位有着全方位的贬损。在这个时代的整体意识形态中,女性应该是受到莫大歧视的。再者,由于10-11世纪的纯净教会的克吕尼改革运动以及本笃教规的盛行,直到13世纪托钵修会的兴起,中世纪的宗教虔诚度不断提高,而在其中,女性的宗教热情往往不输男性,许多女性圣徒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众所周知,宗教虔诚的提升,即使排除其强烈的厌女症因素,至少对于性和婚姻都是持贬损态度的。对于正统教义而言,守贞是义务,婚姻也只是为了繁衍后代的使命而不得不为之恶,任何不以生养后代为目的的性行为都是可耻的,更不用说偷情出轨这种即使现代人看来也无法原谅的行为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在这种压抑女性的氛围中,推崇女性、呼唤爱情、赞美婚外情的骑士文学与典雅爱情这朵奇葩,是如何生长出来的呢?而像兰斯洛这样服从女士的骑士,爱情的骑士,这个非同一般的群体是真的存在?还只是纯粹文学创作的结果?
对此,法国史学大家乔治·杜比看法的接受度比较高。他在《中世纪的爱情与婚姻》(Love and marriage in the Middle Ages)一书中提到了11—12世纪中欧洲发生的两个重要趋势:其一是直系模式的逐渐流行,从多子继承制到长子继承制。公元1000年后,贵族的世袭关系变成了男性世袭。但直到11世纪末,只有在城堡主的范畴内,才开始有更加青睐长子的措施。子嗣间平等关系的观念是相当顽强的。通过不同的方法,以联合财产,限制结婚等措施,贵族世袭在11世纪逐渐扭转了继承分割的危险。这些家庭坚强地捍卫着自己的经济地位,使得在将近两个世纪内,庄园制社会相当稳固。其二是一些家庭内的态度的转变。将家产分割并置于女性管辖下变得越来越难,出嫁女儿不再分得遗产而只有一份嫁妆,使得人们一定要嫁出所有的女儿,这也提高了嫁妆的重要性。
这些变化的影响非常广泛,长子继承导致12世纪的法国北部成了年轻骑士(juvenes)的天下,这些没有继承权但却荷尔蒙满满的幼子们幻想通过冒险找到爱人,并且急切想要得到一个地位高财产丰富的女继承人。同时,嫁出所有女儿和只让长子娶妻导致了女性的供给大大超出了婚姻市场的需求。
这些年轻骑士中许多人居无定所,作为次子而没有获得土地和遗产的希望。杜比认为这种热衷冒险和求得荣誉的攻击性活力是封建社会的组成部分,它决定了宫廷和骑士文学的特点。
但光是勇武的骑士,是没有办法构建出骑士文学这样细腻的精神产品的。就在彷徨的骑士寻求安慰与归属的时刻,另外两种人恰到好处的登场,终于酿造出了“骑士精神”这坛芳香至今的美酒。
贵族圈里人手一册

《玫瑰传奇》插图。《玫瑰传奇》由让·德·默恩创作于 13 世纪,作者采用第一人称,把自己比作故 事中的“情人”,在梦中来到一个美丽果园,为赢得“玫瑰”的欢心,经历了种种冒险。该书是骑士文学推 崇女性、呼唤爱情的代表,在贵族圈里尤为盛行。
这两种人就是任何文学作品的两端:作者与恩主。
关于谁是骑士文学的作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论,因为这个群体本身就包含广泛,游吟诗人(troubadours)、宫廷诗人、宫廷教士,甚至宫廷贵妇本人都写出过出色的文学作品;但是关于谁是骑士文学的观众和推动者,则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人们很想当然地会认为,既然是萌发于宫廷的传奇故事,自然是有宫廷贵族作为恩主支持,并据此提出恩主制的说法,虽然没有明确的事实表明有一部作品是明确献给某位恩主的,大多数情况下,诗人的题献都是为了体裁的缘故或者是为了巴结贵族的缘故而写就的。
但如果没有像香槟的玛丽,阿奎丹的埃莉诺这样的恩主扶持推广,像克雷蒂安这样的职业作家,像安德烈神父这样的神职人员要获得文学成功根本不可能,宫廷骑士文学的随之盛行也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作者和恩主双方并非是一拍即合的。有证据表明,在很多情形下,贡献出骑士文学的作者以及聆听这些作品的观众都不是专门只好这一种体裁,有的作者会写方言抒情诗,但因为其所受的教会教育,可能更擅长拉丁语诗歌,还有的可能会撰写有配乐的诗歌;而宫廷里的观众们(主要是贵族妇女)也可能挑选出自己中意的文艺类型,并不一定选择骑士文学。骑士文学很有可能是在作者与受众双方不断的磨合下慢慢综合形成的一种文学题材。
作为恩主的女性们,在一开始可能并没有特别青睐这种颠倒传统男女地位的文学形式,但渐渐地,她们内心深处对于女性地位及受到约束的不满,甚或女权意识的觉醒使得她们开始喜欢上了这种将她们视为无比崇高存在来膜拜的骑士文学。在这些故事中,她们得到了勇敢英俊聪明体贴的骑士们百依百顺的关怀。没有将自己当作商品买卖的父兄,没有无情无义、纵欲偷欢的丈夫,也没有让人烦恼的家务与政务琐事,她们要做的,只是享受服侍、陶醉于爱情之中、不断获取骑士们的追捧。在投射与移情的作用下,这些女性恩主很快就体会到这种新文学的甜蜜,她们的支持也随之而来了。
不管怎么说,骑士文学与典雅爱情(宫廷爱情)最终还是盛行了起来。在当时西欧的贵族圈里,以爱情为题旨的骑士文学可谓是最炙手可热的。
即使是在那个没有印刷术,主要依靠手抄本流传的时代,像安德烈神父的《爱的艺术》以及让·德·默恩的《玫瑰传奇》在当时的贵族圈里也几乎是人手一册,动辄上千本甚至数千本的销量对比当时西欧贵族的人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可以说,骑士文学与典雅爱情的意识形态影响了整个西欧的贵族阶层,其对后世的影响之巨,从中也可以做出估量。
绕不开的作者与恩主
谈到骑士文学与典雅爱情,有几个人是绕不开的。
首先就是《囚车骑士》的作者特鲁瓦的克雷蒂安,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几位传奇作家之一以及宫廷爱情在法国北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第一个讲述了桂乃芬与兰斯洛之间的绯闻,第一个写作关于圣杯的冒险故事,甚至可能是第一个歌颂特里斯当(Tristan)与伊索尔德(Isolde)的爱情悲剧的人,他是中世纪传奇的主流——亚瑟王系列(Athurian Cycle)的主要奠基者。其作品的影响深远,我们可以从13世纪中叶大量的冠以“兰斯洛—圣杯”或者“通行系列”(Vulgate Cycle)之名的简编散文中感受到,并且他对后来的集大成者马罗礼爵士(Sir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克雷蒂安作品受欢迎程度可以从至今仍然保留的300多本手抄本中窥见一斑。
另一个值得一书的人物是安德烈神父。
关于他,除了他书中的说明,我们一无所知。此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称是“王室的宫廷神父”,曾任职于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中,可能也曾在香槟伯爵的宫廷中效力,而彼时,香槟是当时的骑士爱情文学和拉丁语文学的中心。他的拉丁语作品《论爱情》(Deamore)的前两卷对女性满是溢美之词,教导年轻人认识如何追逐爱情,但第三卷却转向了摒弃爱情的立场,并对女性恶毒攻击。但这种自相矛盾的文风多被认为是戏谑和嘲讽,而且可能是对奥维德(Ovid)的古典作品的模仿。不管怎么说,这部作品都证明了求爱、婚姻和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值得探讨与检验的问题,而且当时也没有第二部作品能够像《论爱情》那样详细地告诉我们,关于爱情主题的讨论对12世纪宫廷社会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位对宫廷骑士文学的盛行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物,虽然不是作家或诗人,但却是这种文学与意识形态在向整个西欧推广过程中的一面旗帜。她就是阿奎丹的埃莉诺,绝无仅有的集女公爵、法国王后和英国王后等头衔于一体的女人。关于她曲折的身世,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我们只要知道因为波云诡谲的政治,这名富有、机智而美貌的女公爵被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英法两国的外交内政当中,但也是因为这种机缘巧合,她把源自阿奎丹公爵领地的文学艺术之风吹到了英法两国的宫廷。须知,其祖父就是现在能够确认的第一个游吟诗人,阿奎丹公爵威廉九世,有这样一位浪漫而富有文学才华的公爵,阿奎丹后来被人称为“爱之地”也是顺理成章的。埃莉诺对宫廷文学的情怀并不亚于其祖父,而身为掌握权力的女性,她更钟情于宣扬骑士为女主人服务的骑士爱情文学。她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财力来资助不少作家、诗人来她的宫廷为她创作,其中最著名的就包括了特鲁瓦的克雷蒂安以及创作了12首莱歌(Lais)存世的法兰西的玛丽。她独一无二的身份以及对典雅爱情文学的钟爱,使得她成了这种文学形式以及意识形态的最佳庇护者与推广者。
当然,根据杜比在《中世纪的爱情与婚姻》的说法,王侯们支持典雅爱情的态度背后还有自己的目的。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提高了骑士的价值到达了炫耀、虚荣和幻想的地步,稳固了骑士阶层的优先地位。典雅爱情是宫廷才有的行为,是优雅的主要标准。另外,这可以用来控制年轻人的非秩序因素而变得驯服,因为它是一种温顺谦虚的教育。而在其中,教会也希望能够发挥能量,由此,一些如安德烈神父这样的神职人员厕身宫廷文学圈中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不管怎么说,大力支持的恩主和才华横溢的创作者,加上年轻骑士荷尔蒙无处发泄的适合发酵的土壤,骑士文学、典雅爱情,生根发芽了。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骑士文学与典雅爱情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西方厌女症传统的延续,虽然形式上是女性占了主导权,但整个故事还是以男性为中心,以其英勇、智慧、忠诚而成为受到赞美的主体,将最后抱得美人归作为他的犒赏。因此,女性还是作为一个“他者”,一个骄傲任性、难以满足的被动的“客体”,男女之间的主从关系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改变,反而因其伪装而更深得人心。
因之,即使西方厌女症传统并没有因为宫廷骑士爱情的理念而有多大改观,但取悦女性这一套路却流传了下来。在这种表演中,男性自信自满,自认为是采取行动的主体,在彰显男子气概同时又因其谦卑绅士的表象而沾沾自喜,虽然降低自己的身份为女性鞍前马后效劳,但实际上,在潜意识里却认为自己仍然是掌控局面的人,依然是双方关系中的主体。
尽管受到女权主义的批判,但从对后代的影响来说,宫廷骑士文学对爱情的赞美与颂扬起到了承接奥维德传统、打破宗教禁欲主义的禁锢的作用,加上其经常会对个人意志与自由进行讴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跨越13世纪初因为阿尔比十字军造成的损失而连接到但丁、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的复兴传统,因为随着法国南部的游吟诗人据点被十字军摧毁之后,诗人们流亡到了各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西西里和意大利成了新兴的文学中心。比如14世纪早期,游吟诗人在意大利创造了所谓的“甜蜜新风格”(dolce stil nuovo),但丁,就是用它形容情歌特有的精致而动人的语言。甚至在德意志,受到游吟诗人传统影响的乐手诗人(Minnesingers)的作品也对骑士之爱赞赏有加。
当莎士比亚写出《罗密欧与朱丽叶》遭到禁止的爱情时,当瓦格纳重谱《崔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悲剧时,当爱德华六世不要江山要美人时,又有谁能说,这不是中世纪的骑士爱情在历史中浅声吟唱呢?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8年16期 谢焕
文章末尾固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