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继愈是我国哲学宗教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在佛教方面的研究成就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他精于学问,不攀龙附凤,不趋炎附势,始终保持实事求是正直谦虚的节操。他一辈子以国家社会需要为己任,无论在治学、教学,还是执掌国家图书馆的各个领域,均有重要贡献。
大智将启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一个中等家庭。其实,任家祖上曾经也属殷实富裕之家,但任继愈祖父在和几个兄弟分家之后,因生意失败,而致家道中落。任继愈的父亲任箫亭出于经济考虑,报考了费用较低的保定军官学校,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刘峙、顾祝同等是同班或同级。任箫亭后来官至少将,但由于生性耿直,不屑弯腰折桂,一直被国民党嫡系部队视为“异己”。1945年4月,他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到张自忠的部队,参加了抵御日军的“老河口战役”,之后转任参议闲职。
任继愈自己则认为,父亲报考军校,其实还有冲出封建家庭樊篱的另一层意思。任家是一个大家族,四代同堂,有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封建家庭的特点就是封建家长制,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不能违逆,婚姻不能自主,诸如此类。任继愈认为,父亲在那个环境下很受束缚,于是没有受限于任家的世代书香门第,选择离开家庭,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成为任家第一位行伍之士。
不过任箫亭仍然喜欢读书,属于文武兼修的“儒将”。他迎娶的夫人、任继愈的母亲宋国芳,出自平原县一户乡绅家庭,她在50岁时开始学识字,后来竟能与远在他乡的儿子们往来书信。在父母的影响下,任继愈和几个兄弟自小就懂得学习和做人的很多道理。
后来,任继愈一家人在鲁南一带自立门户。任父远在外地从军,任母独自担起家庭重担。这位坚强的女性,用她深沉博大的母爱,呵护着小继愈兄弟几个。有一次,尚在吃奶的小继愈得了重病,医生开了汤药。母亲给他喂药时,小继愈的脚不小心把药碗踢翻了,汤药泼了一地。母亲连忙趴到地上吮吸汤药,再变成乳汁喂给他。这件事任继愈终生铭记在心,直到他90多岁高龄时,还常常回忆,每每讲起,眼泪盈眶,他说:“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
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平日非常严格、节俭的母亲,却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文化教育。任继愈4岁入私塾,每每遇到连父母都不能解答的问题时,小继愈知道,书本里有个神奇的世界,那里会有他想揭示的一切事物的答案。有人说,任继愈从小养成的那种刨根问底的习惯,正是他日后成为一代哲学大家的基础。宋代理学家朱熹小时候也是如此,当他父亲用手指着天,告诉他上面是天时,朱熹马上问:“天上面有什么?”这就是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他不仅想知道事物的表面,还想知道事物的本质和背后。自由宽松的家庭环境、专注思考的学习态度、热烈执著的求知欲望,让小继愈日益养成了哲学家所需的素质和思维方式。
芸竹之缘
还在1941年,已经在西南联大担任讲师的任继愈,有一个北大哲学系的同学名叫王维澄,此时正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其妻在联大附中教书。有一次,他的妻子生病请假,王维澄便请任继愈代为授课。当时,任继愈觉得有些为难:依理说,老朋友出言求助,理应责无旁贷,但他认为自己是学哲学、教哲学的,而王维澄的爱人却是教语文的,隔行如隔山,自己能胜任朋友之托吗?任继愈真的有些踌躇。但他毕竟架不住老同学多番恳请,便硬着头皮答应了。好在,王维澄的爱人教的是小孩子,教就教吧,试试看。
不想,这一助人为乐,竟成就了他一生的一段佳缘。
原来,其时在联大附中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叫冯钟芸。她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学术家族:父亲冯景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人;大伯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当时是联大文学院院长;姑姑冯沅君是文学史家和作家,鲁迅曾称赞她是与庐隐、凌叔华、冰心齐名的“五四”才女,后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一级女教授;堂姑父张岱年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堂妹冯钟璞(即宗璞)也是作家,著有《红豆》《三生三石》等。据不完全统计,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级的人物就有30多人。而在家乡河南的唐河,冯友兰和他的弟弟妹妹则被称为“冯家三兄妹”,名闻遐迩。唐河乃至整个南阳地区不但因冯家而感到骄傲,还因之形成了一种好学求知的良好风气。
冯钟芸就出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自然深受熏陶,她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语文教育家。
任继愈帮人带的这个班,正好在冯钟芸所带班的隔壁,并且同是教语文,这样难免有些接触,一来二去,两人就熟识起来。
似乎老天也要玉成这段姻缘,1943年,冯钟芸又被聘到联大中文系当了助教,成为西南联大第一位女教师,与任继愈的接触愈加频繁起来。
当时,联大中文系不仅有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这样著名的学者,中文系还有一部《四部丛刊》。任继愈研究中国哲学史,觉得《四部丛刊》很有用,便经常去借书,正巧冯钟芸也到那里借书。两个年轻人因为有了前面的基础,此时相见,便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更为巧合的是,任继愈还经常去冯钟芸的伯父冯友兰先生那里探讨哲学问题,也常常与冯钟芸不期而遇。
这以后,两个年轻人的心越来越近。
可是,看上去,这两个年轻人又似乎并不急于谈婚论嫁。这让任继愈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很是着急。于是,汤先生亲自跑到冯家,代表任继愈的家长(当时任继愈的家人都在山东或武汉)去谈这件大事。汤先生提亲很郑重,那时人们大多穿长衫,汤先生还特别加了一件马褂,登门到冯家去提亲。实际上,1943年春天,任继愈的母亲刚刚去世,一是他甚为怀念母亲,二是为母亲服孝期间,因此任继愈绝口不提婚姻之事。
联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北大的罗常培先生,对任继愈的印象甚好。而冯钟芸就在罗常培的系里当助教。很快,汤、罗两位先生便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汤用彤有时家里请客,便同时邀请任继愈和冯钟芸两人去吃饭;罗先生则请他们逛逛昆明滇池公园,这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人都心知肚明。这么一来,他们的来往就更多了起来。于是,在先生们的主持之下,任继愈和冯钟芸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证婚人就是罗常培先生。此后,任继愈和冯钟芸一生相濡以沫,一起度过了六十年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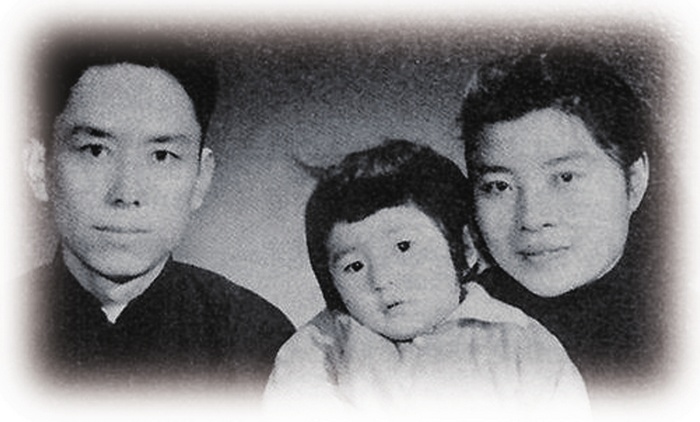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是流行早婚,甚至娃娃亲的。任继愈小的时候,家里也给他定过亲,但他稍长后,坚持要自己寻找爱情,顶着家庭压力,硬是把婚退了。他也从未见过父母给他定的那个女子。
冯钟芸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除却工作之外,冯钟芸还笔耕不辍,并于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杜甫研究论文集》,人物传记《庄周》《屈原评传》《杜甫评传》《贯云石》,以及散文自选集《芸叶集》等。
授业北大
1948年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南苑机场,专程接胡适等一批高等学府文化学者。偌大的总统号,只接走了胡适夫妇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任继愈与众多教师——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郑天挺、沈钧儒、张岱年等等,均毫不动摇,满怀希望,留在了北平,他们和欢欣鼓舞的人们共同迎来了北平解放。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最高学府的雕梁画栋和远处西山的夕阳剪影,成为他们一生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教师上课,还保留着西南联大的传统:没有统一的教材,而是依照各自所长尽情发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仅以语言课程而言,王力教古文,魏建功讲音韵学,朱德熙讲授语法修辞。文学课则更丰富多彩,游国恩讲先秦两汉、诗经楚辞,林庚讲魏晋南北朝、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元曲,吴祖缃讲明清小说和《红楼梦》。外国文学更是不得了,曹靖华讲苏俄文学,季羡林讲东方文学,李赋宁讲英国文学,冯至讲德国文学,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讲法国文学。名家云集,各有所长。
当时的学术教学环境,正如风光旖旎的燕园一样,令人赏心悦目,沉醉其间。知识分子如同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任继愈感觉一下子去掉了臃肿的冬衣,换上了轻薄的春装一样,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也是从这一年起,任继愈兼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此时,任继愈和冯钟芸有了两个孩子,儿女双全。女儿叫任远,儿子取名任重,“任重而道远”,任继愈不仅将自己的一生追求时刻铭记,而且也在下一代身上寄托了希望和祝愿。
这段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生活稳定,任继愈又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对社会历史和思想的关系看得比以前更加清楚了,对任继愈来说,这是个读书和研究的好时机。此时的任继愈年富力强,白天和晚上都要上课、开会、学习,往往是家人都睡了,他还没有回来。孩子们好不容易看到任继愈回来,吃过晚饭后他又埋头去看书、写文章。当时住的是平房,冬天各家都靠小煤炉取暖,一开门,仅存的一点热气都跑光了,深夜里更是寒气逼人。为了熬夜工作,任继愈设计了一张小炕桌,他坐在床上,盖上被子,腿伸到小桌子下边,头顶上方再拉过来一个灯泡,看书写字就不冷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撰写了不少课堂讲义,也完成了许多学术专著。
任继愈的教学和治学一样严谨。一个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任继愈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作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把书稿先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绝不随便吹捧人。而在教学时,他采取平等的态度来研讨,跟学生在一起也特别随便,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强迫学生接受他的观点。任继愈经常对学生说,他非常佩服司马迁,让大家都学习司马迁。他说,司马迁被汉朝统治者迫害,很惨,应该说汉朝对不起他,但司马迁写史尊重史实,写了汉代的繁荣、升平,并没有借机报复,歪曲、篡改历史。“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尊重历史”。
任继愈培养学生,注重思想方法等根本问题,曾有学生问任继愈,他应该学习佛教的哪个派别。任继愈说:“我们去颐和园,都是先上万寿山、佛香阁,看了颐和园的全景,再去谐趣园、十七孔桥,对不对?没有一进门就往谐趣园跑的。学习、研究一门学问也是这样,首先要掌握这一学科的全貌,整个的历史,把基础打好,再去研究某一派别或某一断代。你现在不要忙着想什么宗派,把基础的中国史、世界史、佛教史以及佛经都多读几遍,弄通如道教史、基督教史等,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再考虑具体的研究方向。”
现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博回忆说,“大家都有个重要印象:任先生为人十分谦和、低调。我觉得,任继愈的所有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名学者,而且是有古风的学者。任继愈生命中有刚毅、柔韧的气质,说话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做人有原则,很坚持。此外,任先生也是有现实关怀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理都包含了现实的关怀。在做学问方面‘择善而固执之’,体现了北大哲学系的开放精神。”任继愈门下弟子众多,李泽厚、余敦康、张岂之等在上世纪80年代早已盛名在外。

凤毛麟角
任继愈是最早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任继愈主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他说:“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回头来再剖析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开此先河,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继之,随后又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整个20世纪50年代,哲学界纷纷开始服膺马克思主义。
任继愈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逐渐摸索出一条以释、道、儒三教相互影响为切入点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道路。由此,他走出了一条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治学道路,使他的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别开生面,自成一家。任继愈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视野观察宗教问题的先河。
他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以举出以下几种特点和品格:不失自我的兼容性、与时俱进的应变性、取之有节的开发性、刚柔相济的进取性、和而不同的自主性。但最突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善于吸收一切有价值的外来文化,融入固有文化主流,不断发展,几千年沿着既定的方向,走着自己的路。中华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从来都是以自己固有的思想体系、思维模式来迎接外来文化的。
佛教等几个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及其发展道路,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色。佛教最先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天竺来,中国人所认识的佛教经典都是根据西域文字翻译成汉文转手引进的,一度佛教在中国被看作是黄老清静无为的理论,而中国最早介绍佛教的著作《四十二章经》及《牟子理惑论》,都以中国传统忠孝观念来理解这一外来宗教。景教(西方基督教的一支)在唐代最初传入中国,中国人认为这个教派“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这完全是当时唐人的新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中国学者也著《天方性理》,以迎接这一外来教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理解。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宗教的忠孝观念得到一切外来宗教的认同。后来的儒佛道三教会同,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圆融无碍、海纳百川的特点。研究佛教不知不觉与儒、道两家会合;研究儒教又必然与佛、道两家贯通;研究道教又必然与儒、佛两家相会。
正是在唯物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任继愈从新中国建国之初开始,就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重新建立中国哲学史的论述体系。20世纪50年代,任继愈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那时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任继愈和他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后来便有了在中南海与任继愈一席长谈的佳话。任继愈是最早为毛泽东所注意到的哲学史家,他的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其实,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关注的,但这一点任继愈先前并不知晓。后来,受邀与毛泽东谈话,对此体会渐深。任继愈过去写的一些关于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基本都了解,且都认真看过。毛泽东对任继愈一直评价很高,在《毛泽东文集》中留有这么一段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伊斯兰教的没有见过。”
这就是毛泽东说任继愈是“凤毛麟角”的由来。
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众多研究所里,增加了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任继愈主持筹备并一直担任领导工作。研究所当时设在北大,参加者有中宣部的理论专家于光远、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国务院宗教局局长肖贤法等。时年48岁的任继愈出任所长。工作开展以后,研究所又办了一个刊物,叫《世界宗教研究》,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群体哲学
任继愈在研究宗教的同时,也没有停下研究哲学的脚步。在谈到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时,他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吃饱喝足后就安静了,人的好多问题却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产生的。人需要关心自身最终的结果,渴望了解死后的生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宗教,另一个是哲学。宗教向人保证: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没有任何怀疑;而哲学是理性思维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脱的道路,但不保证人人都可能最后解脱,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学关注生存群体的解脱,关心集体,关注弱势群体,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怀。
很多人认为,任继愈的哲学研究是一种“精英哲学”,而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种“平民哲学”的研究,所以,虽然有很多人知道任继愈,却不知道任继愈的哲学思想。任继愈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研究的不是所谓的‘精英哲学’,也不是什么‘平民哲学’,而应该是群体哲学。我不想离开群体去标新立异,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做好一件事。”
其实,正是在“七七事变”后1938年的那次西南大迁徙中,任继愈看到了中国的现实,才更加坚定了终身从事哲学研究和思考的方向。而且,他也一直以结合中国国情为原则,以探索国家和社会的出路为己任。任继愈的群体哲学还体现在,他将研究的触觉伸到了影响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琐碎问题。比如他在1956年便开始提醒政府注重中国本土医学的开发和科学利用,并为此写了一篇名为《正确对待中医》的文章。更有趣的是,他还提醒政府要注重人才的选拔与流动,并在文章《创业人才与守业人才》里利用古今事例进行对比,以示警惕。怪不得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评论他是一个“疯狂工作,并忘记自己存在的可爱小老头”。
任继愈说,哲学的起源也说明哲学家不能只停留在书斋。有一次,任继愈在回答记者关于哲学的现实意义的问题时,他谈到,人类自从认识了自身的存在和它的独特价值,就开始了对社会、个人的作用进行探索。人类与自然界打交道已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认识自己、探索社会成因、如何在群体中生活、建立人际关系的规范,最多不过几千年。这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哲学萌发得很迟,但它又是人类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民族有文化、有艺术而没有哲学。没有文字就没有哲学,因为哲学是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至于人类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创造,使人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工具,用它来观察历史现象,分析社会现象,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进程方向,从此不再陷于盲目。而在研究哲学的方式方法上,任继愈也有自己的特色。从步入学术界那一天起,任继愈就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这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紧密的联系。作为一位与新中国历史同步的人,任继愈经历得太多,他的心,始终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任继愈的学术态度是治学要独立,效果要为公。
他曾说:“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他们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前者不平则鸣,毫无畏惧、永不妥协;后者淡泊名利,荣辱不惊、天然本色。如前者不易,如后者亦然。“我佩服鲁迅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指出,不妥协,不和稀泥,这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居里夫人是难得的可以克服困难,又可以经受成功考验的人。成功、名誉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内心,她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时刻不忘祖国,将自己发明的元素命名为钚,以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这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任继愈的学术研究明显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倾向。比如中国是一个宗教大国,每一名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受“儒、道、释”三家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他受毛泽东所托研究“佛学”,可以说任继愈的学术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学术。难能可贵的是:任继愈精于学问,不攀龙附凤,不趋炎附势,始终保持节操。
有记者问任继愈:哲学对于您自身的意义何在?任继愈是这样回答的:“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多帮助别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机遇和外部环境条件。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成绩不是最拔尖的,不过也不是最差,算个中等。但是我有上学的机会而别人没有,这是我的机遇。后来我考上大学,这也是我的机遇。别人求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应该回报社会。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从里面舀水,你还得往里面加水,这桶水才不会枯竭。”
平日与朋友交谈,除了学术交流,任继愈说得最多的都是国家大事。朋友问:“一辈子研究宗教,您信教吗?”他慨然一笑:“就是要不信仰才能研究,我是无神论者。马克思说过,如果跪着看谁,谁就一定比你高了!”若让他谈谈自己,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每到关键处,任继愈总是轻巧地把话题岔开。他强调得最多的是,与他人相比,自己并非最出类拔萃,都是机遇。他说:“如果没有社会的培养,就没有个人的成材。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劳记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岁的时候编了《中国哲学史》,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样能编出来。如果我就此忘乎所以,以为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了,这和我的实际情况不符。”任继愈不认同别人认为他是颇具影响的哲学家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将来一定会诞生伟大的哲学家,但那需要一定的条件。他说,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哲学家,应该说他要能够涵盖世界上的根本问题,要有说服力、有征服力,能使人信服。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这个条件。哪一个宗教也做不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哲学家了。中国难出哲学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关系。借鉴西方本来是好事,但把握不好,就成了依样画葫芦,生搬硬套,先是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后来又生搬苏联的。实际证明,这种方法无助于弄清哲学的本来面目,反而增加了混乱。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制约哲学家的出现及对哲学思想的认同。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也是后来才影响世界的,当时他们也影响不了,后人才拿他们作旗帜,马克思也是如此。文化是一种积累,思想有超前性和滞后性,不是亦步亦趋,于中国更是如此,需要一个过程,相信以后中国一定会有人成为影响世界的哲学家。

国图岁月
岁月如梭,转眼之间到了1987年。从1964年受命组建宗教研究所,屈指算来,任继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已经工作了20多年。是年,任继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被称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从此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
这一年,任继愈71岁。
任继愈爱书,爱藏书,是出了名的。走进任继愈先生的家,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贴墙而立的一排书柜。任继愈告诉造访的人,这是清末一个藏书家的书柜。其弟子变卖了柜子里的藏书,最后连柜子也要卖掉,他便买了下来。任继愈爱书,对藏书家的柜子也格外珍惜,柜子里放的都是他最珍爱的图书。然而,在任继愈晚年,书柜里的书却渐渐少了,每年都有一些书被他运走了。原来,这些书的新去处是任继愈的家乡——山东省平原县图书馆。他说“:我从念高中开始到北京,就没怎么回过山东,把它奉献给养育我的土地,心里踏实一点。”任继愈还说,让书本给更多的人翻阅,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
现在的图书馆学界和图书馆界,有一种图书馆存在悲观论,这种理论和声音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信息和文献的需求,不再似过去那样依赖图书馆,人们可以不利用图书馆或不到图书馆就可获取所需要的文献和信息,并且最终有一天会不再需要图书馆,图书馆将在人类社会中消失。对此,任先生有他个人的深刻思考,在2009年接受《中国图书馆学报》专访时,任老说:“图书馆是一个长寿的机构,即使国家消亡了,政府没有了,但图书馆会存在。方式可以不一样。因为知识总是有的,求知总是有的。”任继愈说,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记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轨迹,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宝库。他说:“图书馆作为收集、加工、存储各种图书、资料和信息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在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全民终身学习和教育的基地。图书馆可以不受年龄、学科的限制,为读者提供所需资料,起到解决知识匮乏的作用;图书馆虽然不直接创造财富,却间接培养创造财富的人,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的教育职能不同于大学,责任要比大学大,服务的范围要比大学广,服务的层次要比大学深。”
国家图书馆的定位,一直是图书馆界关注的重点。作为馆长,此一问题是任老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在任继愈眼里,图书馆是一项公益性文化事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贡献是长期的、与时俱进的。因此,国家应当加大投入,不求直接回报,不应该把图书馆等同产业去经营。当然,公益服务不等于免费服务。图书馆可以根据不同的职责,秉承公平的原则,向公民提供一定层面上的免费服务。对有些超常成本的服务,收取一定的成本费用是合理的,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采用的方式,这仍属于公益性服务的范畴。在2009年《中国图书馆学报》访谈中,任老在谈到他任馆长以来国图的发展变化时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过去我们馆偏重文献资源的收藏和整理,流通考虑得少。我来之后,在努力扭转,越是希见的东西,越要跟社会见面,不要锁起来。重藏轻用的局面现在已经得到了改善。”
他还身体力行领导了空前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依托国图的馆藏,整理古代文献。他历时十余年,以国家图书馆馆藏《赵城金藏》为底本,主持编纂107卷《中华大藏经》。就在去世前他还在主持规模达2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编纂工作。2004年,看到世界范围内收藏的敦煌文献都已陆续出版,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却由于经费原因不能面世,任先生心急如焚,致函有关部门:“今我国力日昌,倘若国家对此项目能有一定的投入,我愿意尽我九旬老人的绵薄之力,使这个项目在3年左右的时间全部完成,还敦煌学界能完整使用资料的一个愿望。”在任先生的主持下,如今150巨册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陆续出版。此外,他生前还主持着《中华大典》的编纂和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为了让国家图书馆珍贵的馆藏得到社会的广泛使用,他说,他整理古代文献,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也是他作为馆长的一份工作和责任。他预测,中华民族文化的鼎盛期可能要在20年后到来,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做一些文献的积累和整理工作,为文化高峰期的到来打基础。这就是一个以文化建设为己任的老人的拳拳之心。
在清理传统遗产的工作中,任继愈是付出精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从儒教,到佛教、道教;从哲学,到宗教,到自然科学,还有其他如文献学、民俗学等等。传统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任继愈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过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导。23年前,任老刚刚上任时所担心的设备一流、图书馆的实力未必一流的现状已不复存在,国图现在已经迈进了国内外一流图书馆的行列。
一个心愿
在一次与记者谈话时,任继愈透露:他想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在他的构想中,这部哲学发展史与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主编的4卷本《中国哲学史》大不相同——不是教科书,全部是他个人研究心得。“不要太长,大约30万字。”任继愈计划着。举重若轻,不慕虚华,正是他的学者本色。要把几十年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浓缩在30万字的篇幅中,难度不言而喻。在不少学者以“著作等身”为荣耀的时候,老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此,老人的思量更为久远:“历史上有很多书,号称学术著作,却没有学术性;号称科学著作,却没有科学性。因缘时会,也曾时行过一阵子。时过境迁,便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主持这个淘汰选择的就是广大读者。天地间之大公无过于斯者。我自己写书,希望它的‘寿命’能长一点。”
但他最终未能完成这部只有30万字却令人充满期待的大书。
枯燥浩繁的整理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因为,在他的案头,总有看不完的书稿。而与自己的著述相比,他永远把这些书稿排在更加优先要处理的位置。《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无一不是鸿篇巨制。的确,时间宝贵。任继愈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他只得把自己的写作计划暂时搁下。正因为如此,任继愈著述一部带有自身学术总结性质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计划,被一拖再拖,一延再延,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学界,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但对于任继愈,却是无悔的选择。早在十多年前,任继愈在给女儿的家书中就曾这样写道:“要相信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中华文明有所贡献。即使不为目前,也要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对社会有用,就值得去干。”而纵观任继愈一生的学术研究,尽管跨越多个领域,但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到:传承中华文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系于心头,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主线。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在北京医院离世。他的遗照两边写着这样的挽联:“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槃,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
(摘编自江苏人民出版社《真理的思考——任继愈传》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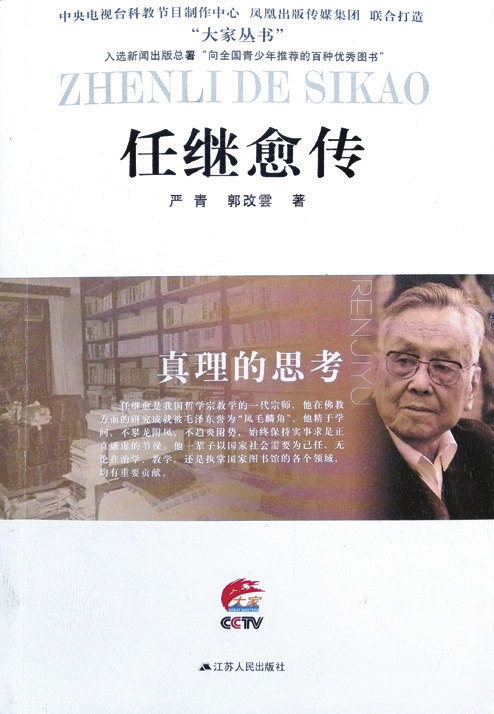
来源:《阅读》2016年47期 严青;郭改雲
文章末尾固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