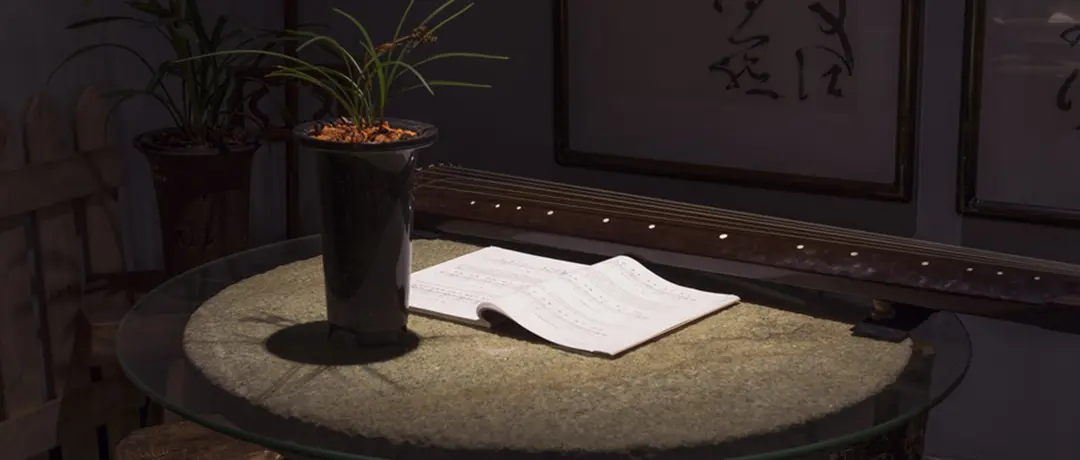
中国艺术批评与鉴赏受老庄的道家思想和佛教的禅宗思想影响,形成了一种超越寻常思辨的欣赏态度。在中国书画作品中充满了“道”“性”“气”“风”“骨”“神”等一些玄妙难言的感受性词汇。故而在这种主观直觉式的评赏方式中,往往需要欣赏者在见到创作者的作品时,能够一点即悟,其艺术修养水平能与作者的创作心理产生暗合。在传统艺术形式中,“文人画”的创作与欣赏尤具此特质。
北宋画家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以“笔简形具”四个字概括了“逸”格的文人画风格特质。去繁入简,复归平淡是文人画家一再提倡的美学思想,落实于画面也成为文人画绘画形式的重要特点之一。张彦远道:“上古之画,迹简意淡而雅正。”张彦远所说“迹简”是指绘画形式特点;意淡则指向作为艺术境界的冷逸之美。简淡是古代文人的绘画审美倾向,也是冷逸之美最为重要的形式特征。本篇欲从文人画家的作品画面入手,探究作为意境的冷逸之美和作为笔墨特征的简约、萧散之间紧密且微妙的关系。笔墨的简约是和冷逸的审美格调共同发展起来的。富贵繁华乃皇室权威的象征,简雅清淡则是文人逸士的雅好。奢侈繁复的艺术风格一般是为装饰而做的,就比如造一座伟大的宫殿、绣一幅艳丽的锦缎或者是画那幅著名的《康熙南巡图》,我们很难想象工匠们如何在这种类似于体力劳动的繁复工作中得到乐趣。督创《康熙南巡图》的王翚也只是将这种工作当作一种工程来完成,从未听说过他在完成这一作业时得到了心性的舒展、生命的安顿。奢侈是通过繁复表现的,正如我曾读《红楼梦》时不解,为何宝玉房中要设这样多的丫鬟用人,一杯水递进房都要经过几道手,且等级不同不可随便僭越。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奢侈,正是在这种繁复的程序和规则中,权力和财富得到了彰显。而文人雅士则不同,他们的艺术是用以安顿生命的,那是一个摒弃了造作和等级的世界,只关于个人性灵,而与财富权欲无关,所以他们不追求技法的极致,并且明确否定了繁复谨细的绘画形式。张彦远说:“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其实,绘画于文人而言是一种抒发情感的语言,没有这种语言无法表达内心,过度追求语言的规则又会阻碍表达,而最好的语言就是言简意赅,于是“笔简形具”便成为画之为逸的要求。
纵观画史,如张彦远所说的上古迹简意淡的雅正之画其实今天已经很难见到,但是有宋以来呈现冷逸之美的文人画作品大多笔墨简练,这是得到公认的。北宋前期山水画在构图上多为全景式,内容和笔墨也比较繁复,但是到了赵令穰等人这里画风一变,多取平远小景,在审美上从气势磅礴转变为优雅别致。大宋南渡之后画风又是一变,最为著名的就是马远、夏圭开创的“边角山水”,真是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而后南宋的禅画更是笔墨精练的典型。首先“简约”是一种选拔,《古汉语字典》中就解释“简”有“选择、选拔”的意思。选拔即摒弃可有可无的笔墨,留下最能表现物象形态的部分,恰到好处才能笔简形具。这种简约的炼成并非易事,这关乎画家对物态以及对象精神的把握,最后留下的那几笔看似草草却天工人代。倪瓒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观倪瓒的作品确实着墨不多却形神俱佳,与道同机。倪瓒画山水先以淡墨勾画,然后点上苔点,这点点墨迹,在石便勾勒出了石头的凹凸,在树则凸显树枝的枯瘦,在山便烘托出山峦的起伏。总之细看倪瓒的作品,几乎都能将线条笔墨数清楚,但是就是这样精练的笔墨勾勒出了一片江南。倪瓒说自己作画只是“逸笔草草”,道出他对待艺术生命的本质体验。恽南田的折枝花卉寥寥数笔便是一片春意。宋代翰林书画院承袭后蜀画风,留下了令人叹服的花鸟作品,其写实程度堪比西方油画作品,但是这样的谨细并非文人所崇尚的。在文人眼中最美妙的作品还是简淡清雅的,正如南田画牡丹都不是大富大贵夺人睛目的样子。虽然今天我们看到署名南田的作品中也有不少看起来颜色艳丽经过多次勾画晕染的作品,但是其中不乏伪作与代笔之作,而能被判断为南田本人亲笔的作品,大多都是着墨不多且有深曲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简约使冷逸在笔墨上得以体现,冷逸亦使简约变得非同寻常。正如意境和形式的不可分离,而在这种笔墨的简约中,崇尚冷逸的画家们游戏着心性,创造出空灵的世界。
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提出,“逸”是“意简神清,空诸功力”,故能从能、妙、神三品脱颖而出。中国绘画精神不是“再现性”的,而是“再生性”的。去除不必要的细节,提炼最本质的精华部分,直达内在生命体验。抛开目之所及的外在美,宣畅内在生命的和谐。就像王维的诗画,简淡空灵,描摹的景象也不是千岩万壑,而是一丘一壑。江村山林,寂寞小景,意味野逸却深幽隽永。可以说王维是这种“以简胜繁”的审美取向转化的代表画家。唐代禅宗思想兴盛,华严哲学流布。华严哲学提出的“一无量,无量一”和禅宗的“悟则当下便恒,拟思便差”都关注微观简致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细微处可以照见大千世界,一物可以蕴含万物之理。万象纷然,参而不杂,一切即一。简约是文人画审美的重要内容,“简”不是简单、空泛,而是剥落尘埃,透出生命真象,解除知识的葛绊、世俗的机巧,淡然自足。这是中国艺术的独特境界,天地幽微之情可表苍茫宇宙之韵。文人画的“折枝”与“汀渚坂坡”最能将这种境界表达出来,一幅小品中几片叶子也有俯仰之意。于一小微尘,即见溪山无尽。马远、夏圭多作寥寥一角,微微一隅,或孤舟泛月,或远汀微茫,绝壁参天,简洁率逸又意蕴无穷。
简处见大千,中国文人在体验万物的过程中,对物象做了深化与净化。一叶知秋,是集哲思与审美于一体的生命本体。要求画家在取象时必须超越纷纷扰扰的世事,高蹈独步,不以造物所累,不以形为心役。所谓“去物”,就是一个简到极致,增一笔而嫌多的完美艺术形象,其中的“弃绝”自是历尽了“千刀万剐”,去除物象,观其精神,唯愿如此。去除繁复的外在色相,心境玲珑澄澈,方可得以体会天地清旷、月落帆空。“去物”,亦要“去我”,是将自我的欲望淡去,对自我情欲的超越,像庄子所说的“离形”“堕肢体”,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去除自然欲望带来的烦扰,使心灵莹洁光明,一无挂碍。作品也自然风清骨峻,境界超逸。中国艺术精神向来不是召唤人性本能欲望,而是寻求本真,净化升华性灵。简化后的情感是经过沉淀和思省的,激烈的情感躁动复归宁静,内在精神世界被涤荡澡雪。此刻,“真我”之心清净如初,如玉壶冰心,映照万物。
文人画呈现冷逸之美与笔墨的简约不无关系,但是笔墨的简约又不是文人画呈现冷逸之美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苏轼在《书黄子思诗序》中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苏轼赞赏魏晋钟、王的书风为“萧散简远”,又强调其“妙在笔画之外”,说的亦是简约之外别有萧散才是笔墨的至高境界。萧散作为一个艺术批评概念同样来源于道家哲学,那个著名的散木的故事就是萧散这一概念的导源。但是在本文中所谈的萧散不是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出现,而是作为一种笔墨风格来讨论的。中国画是线条的艺术,笔墨主导了绘画风格,萧散的笔墨是冷逸画风在技法上最重要的支撑。实际上即便是不用颜色只用水墨,如果笔墨中无萧散之气,黑白世界仍然是浮躁不堪的,这在当下的许多张狂的新水墨画中都有体现。但是,即便是用颜色,如恽南田用色如用墨,淡彩轻敷,下笔清绝而非艳俗,一样是能够在画中展现冷逸萧散之美的。所以,我认为本章所谈论的,笔墨中的萧散之气,才是冷逸之美在技法上的核心所在。
论萧散的笔墨首先要从书法说起,正如苏轼所说“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有宋一代的文人在书法审美上“尚意”,与唐人注重技术法度的审美态度完全不同。宋代士大夫认为“萧条淡泊”才是近乎自然天成的。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认为,虽然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在书法的艺术创作上有创制之功,但过于注重法度,而显露出人工的痕迹。中国书画的技法在宋代几乎已经接近完善,画院作品的鬼斧神工对士大夫而言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他们要在法度之外追求另一种更为高级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是天真、活泼、疏散。苏轼在绘画上提倡重神不重形,而在书法上则是注重萧散而不重法度。正如历史上那张著名的传为苏轼的《枯木怪石图》,笔墨苍老,神韵枯拙,可谓是绘画作品笔墨中的书家功力。中国绘画和书法本就同根同源,字是象形字,材料都是毛笔和墨,最重要的是文人画的创作主体文人画家都在绘画之外写得一手好字。所谓“画者书之余”,文人画家即便是造型能力不够,但是书法功底总是扎实的。所以,苏轼画枯木怪石,稍稍几笔就已神韵俱备;米芾那著名的米家云山,若不是过人的书法功底,万万是点不成这一片山色空蒙的。宋人书法的虚和萧散,并不是忽视法度,而是在掌握法度之后超越法度。法度在自然无为的笔墨中不露痕迹,这才是高妙之处。宋人对萧散的推崇也是“逸格”能在宋代被推为艺术评论的最高标准原因之一。元代赵孟引书入画,实际上是继承了宋人的艺术精神。明代董其昌也是在理论上提倡萧散境界的重要人物。他以南北宗论画,实际上就是为了推崇以萧散为特点的南画。书法萧散,笔墨亦萧散,画境自然萧散。
来源:《国画家》2022年第01期 马新阳
文章末尾固定信息

